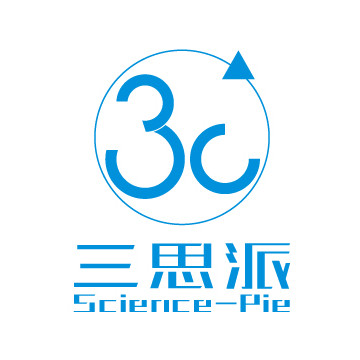科学是如何从牛顿时代几位先驱者的孤独探索,发展到今天这种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活动的?正如天文学家研究星系的诞生与演化,我们是否也该研究科学本身的生长规律?德里克·J·德·索拉·普赖斯(Derek J. de Solla Price)在《小科学,大科学》中以严谨的量化分析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以每10-15年翻一番的速度指数增长,当代活跃的科学家占历史上所有科学家的80%以上。但这种增长能持续多久?当科学经费增长超过科学人数增长,而科学人数增长又超过人口整体增长时,我们是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危机?这本书不是讲述科学家如何发现真理的故事,而是将科学作为社会活动进行量化研究,不仅揭示了科学的过去,更为预测科学的未来提供了工具。
在科学支出占国家GDP比例不断提高的今天,在“无形学院”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全球即时联系的时代,在科学家逐渐从实验室走向政治舞台的世界里,普赖斯半个多世纪前的洞见依然闪烁着前瞻性的光芒,引导我们思考:科学的下一个增长阶段将走向何方?
一、时代背景与成书缘由
《小科学,大科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是一个科学技术迅猛扩张、同时也引发深刻反思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曼哈顿计划”等超大规模科研项目,战后冷战又推动美国和苏联在航天、核能等领域竞相投入巨资。“大科学”(Big Science)作为一个术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美国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于1961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Weinberg,1961),感慨科学研究已从独立科学家小规模作战进入政府资助的庞大战略时代。大型加速器、大型团队协作——“大科学”时代的特征开始显现,人们也开始担忧科学体系自身的发展极限。
普赖斯敏锐地意识到:科学正在经历从“小科学”向“大科学”的演进,但这种演进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他成书的契机,正是要探究这种演进背后的规律。他问道:是什么力量驱动了科学共同体在数百年内膨胀了百万倍?这种增长是否会永无止境?科学组织方式的变化对知识生产有何影响?科学体制的日益庞大会带来什么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仍缺乏系统解答。普赖斯以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为基础,试图对上述疑问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小科学,大科学》既是对时代之问的回应,也是向“科学学”这一新兴理念的大胆探索:用科学方法研究科学自身。在一定意义上,它标志着科学计量学和科学社会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核心内容与主要观点
《小科学,大科学》全书篇幅不长,却思想密集,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科学发展模式的精辟论断。其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2.1 科学增长的指数规律与极限
普赖斯首先以大量史料数据证明,近代科学的发展遵循指数增长规律。从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无论是科学家人数还是科学论文发表量,都以复合年增长率持续攀升,约每10-15年翻一番——意即科学的即时性特征,如今在世的科学工作者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的总和。换言之,在任何一个时间截面上(如1700年、1800年或1900年),当时健在的科学家人数都占到有史以来累计科学家总数的绝大多数。正因如此,他才说出了文章开头提及的那句名言——“80%到90%的科学家都是活跃在当代的人”。
然而,普赖斯指出指数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它最终必然转变为logistic曲线,达到增长的拐点和上限。他以近乎诙谐的方式指出:如果科学规模按1960年代的指数率不变地增长下去,那么不久的将来科学家人数将超过地球总人口,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指数阶段只是科学成长的初期,中长期看应遵循一条先快后慢的logistic曲线,最终趋于饱和。普赖斯将这一推论称作分析科学的“第二基本定律”。他预计,当科学增长开始“拐弯”放缓时,就意味着大科学时代真正来临。“大科学”将成为“小科学”传统世纪与转型后时期之间令人不安的短暂插曲。若我们期望以科学方式探讨科学并制定规划,就应称即将到来的时期为“新科学时代”或“稳定饱和期”;若无此愿景,则只能称之为“衰朽期”。
2.2 科学生产力的帕累托结构
普赖斯重新审视了高尔顿关于科学杰出人物的研究,发展出科学生产力的数学模型,提出科学成果生产遵循“反平方律”,即产出N篇论文的科学家人数与1/N²成正比,揭示了科学内在的精英结构:少数科学家(约10%)贡献了大部分成果(约50%)。进一步地,普赖斯指出优秀科学家的数量以更慢的速度增长(约每20年翻一番),而一般科学家的数量则随其平方增长。这解释了为何随着科学总规模扩大,平均水平会有所下降,以及为何科学精英结构变得更为重要。
为解释这种非正态分布现象,普赖斯引入了“稳固度”(Solidness)概念——用论文数量的对数作为科学生产力的测量单位。他指出,稳固度的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这表明科学生产力遵循费希纳法则(Fechner’s Law)——产出与能力的对数成正比。普赖斯将这种分布规律应用于更广泛的科学结构分析,发现科学具有“结晶化”倾向:无论是科学家、机构、期刊还是国家,都倾向于形成类似城市规模分布的等级结构。大的科学中心、领域和国家往往以牺牲小的为代价而增长。这种结构意味着科学的增长并非均质化过程,而是在保持固定等级结构的同时整体放大。普赖斯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科学内在的“非民主性”,也解释了为何科学资源和影响力高度集中。
2.3 科学论文的发展与无形学院的形成
科学论文的首要功能不是信息传播,而是确立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和优先权(priority)。普赖斯引用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关于科学优先权争端的研究,指出多重发现(multiple discovery)和由此产生的优先权争议是科学史上的普遍现象。普赖斯认为,科学发现的多重性揭示了科学并非像理想中那样通过论文进行有效前沿沟通。如果论文是为了避免重复工作,那么它的效率显然极低——科学家们似乎仍然“蒙着眼睛”工作。因此,尽管表面上科学论文似乎旨在提供前沿信息,但实际上更是一种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确认个人贡献、划定学术领地的社会工具。
普赖斯提出了“无形学院”的概念,即由少数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小型精英网络。这些网络以频繁的人员流动为特征,成员间不断交换前沿观点与未发表成果,通过非正式的互动和面对面的交流,达到超越传统正式学术出版物的高效沟通。普赖斯认为,这种结构有效解决了科学增长带来的交流危机:它将庞大的科学群体缩减为可通过人际关系处理的小型精英群体。无形学院同时具有重要社会功能,为成员提供同行认可和地位,而无需通过增加论文数量来实现。进一步地,高产科学家通过领导团队提高产出,突破个人能力限制,团队模式使更多潜在科学家得以参与,成为“零星作者(Fractional Authors)”,同时保持分布曲线的稳定。
2.4 大科学时代科学家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投入开始出现以往难以想象的加速度增长,科学事业的开支不再仅仅与科学家人数成正比,而是呈现出成本“平方级”上涨的趋势。从全球视野看,许多原先科学基础薄弱的国家,通过积极引进外来教育和人才,往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以更快速度“追赶”甚至超越传统的科学强国。由此带来的科学饱和与资源竞夺,将逐渐形成一种“后指数”的增长模式,改变了原先小规模科学自发、有序演进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科学家群体的权力日益彰显。“无形学院”与精英团队在获取经费、招揽人才上具有更大的杠杆效应,而社会与政府对科学的依赖也让科学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普赖斯强调,随着社会对科学的期待不断提高,科学家必须承担更多公共责任,甚至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而不仅仅满足于“在关键时刻提供答案”。这种“走向政治前台”的趋势意味着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远离权力中心的“象牙塔”学者,而是握有核心资源、也必须对整体社会福祉负责的重要决策力量。
三、科学计量学兴起与当代科学发展的思考
作为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小科学,大科学》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它的许多论断在后来被验证或进一步发展,显示出相当的预见性;同时,也有一些局限和时代烙印,需要辩证看待。以下从当代视角对普赖斯理论作进一步思考和评论。
3.1 理论方法的局限与拓展
不可否认,《小科学,大科学》作为早期探索,受制于当年可获得的数据和理论工具,其结论有一定简化和粗线条之处。例如,普赖斯侧重数量指标,对科学的质变缺乏讨论。他的同代人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关注范式转换、科学认知模式的断裂,这种质性视角在《小科学,大科学》中几乎未涉及。普赖斯描绘了科学“量”的增长轨迹,但对科学“质”的飞跃(如革命性发现如何发生、知识体系如何重组)没有深入探讨。这可能与他的研究方法有关:计量分析擅长总体趋势,难以刻画个别重大创新的偶然性和社会构成因素。
然而,这些局限并没有削弱普赖斯理论的价值,反而在后来得到学界的补充和拓展。科学社会学者综合了普赖斯的量化方法与库恩、默顿等人的质性分析,形成更完整的科学研究图景。例如,对引文网络的分析结合社会网络理论,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知识扩散和学术社群的演化。有趣的是,普赖斯在书中把科学比作一个气体模型(他曾打趣说科学共同体像气体分子一样有总体压力和温度,但个体运动难以预测),这个隐喻预示了后来复杂系统科学对科研体系的研究思路:既寻求统计规律,又承认个体多样性导致的不可预见性。总的来说,普赖斯的理论框架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其核心思想依然具有解释力,但需要在当代语境下与新的证据和理论相互印证、修正。
3.2 科研评价与科学文化
普赖斯的著作启发我们反思科学的价值和评价标准。在大科学时代,传统的同行评议和学术声誉系统仍然重要,但也面临压力。正如前文提到的,定量指标大量涌入评价过程,使得科研评价体系发生改变。随着社会各界对科学的关注和期望提高,科学不仅要“向同行证明”,也要“向社会证明”。应用性和直接效益成为衡量科学的重要标尺之一。在政策层面,表现为对技术转移、专利和产业化的重视,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定向研究”的支持,然而过度的功利导向也可能侵蚀科学探索的根基。普赖斯生活的时代,科学被赋予崇高的求知价值(“为科学而科学”),而如今,科学家常被要求解释他们的研究“有什么用”。如何平衡科学的内在学术价值和外在社会价值,使科研评价既鼓励探索真理又不脱离现实,成为现代科学文化中的重要议题。
科学计量学本身也将目光投向不端行为和伦理等软性方面。因为在竞争激烈、评价严格的环境下,可能诱发学术不端(造假、抄袭)和功利行为(片面追求数量)。科学界近年来加强了对科研诚信的监督,倡导开放科学(开放获取、开放数据)来提高透明度,也属于塑造良好科学文化的努力。普赖斯书中谈到科学共同体和无形学院时强调,科学有自身的文化规范和非正式交流,这在维护科学伦理方面至关重要。今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不是数据和论文的游戏,它需要诚信、协作、批判精神和宽容失败的氛围作为土壤。这类“隐形指标”如何巧妙的衡量,对推动科学计量学在科学学研究中起到关键作用至关重要。
四、结语
六十多年过去了,《小科学,大科学》依然是科学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普赖斯以其“测度一切”的热情和恢宏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图景。书中那些数据背后的洞见至今发人深省。在当代,我们或许具备更多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理论工具,但回望这本书,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思想的力量:对科学本身抱有理性的好奇。这种好奇促使我们不停地追问:科学将向何处去?我们又将如何引导它造福人类?正如加菲尔德在纪念普赖斯时所说:“我们的生命有限,而普赖斯的影响将与科学计量的事业同在,普赖斯是永生的。”
普赖斯的思想穿越时空,怀着对这位先行者的敬意,我们品读《小科学,大科学》,不仅是回顾历史,更是为了更清醒地展望未来。科学之小与科学之大,在这本书里交汇成耐人寻味的对话,而这场对话仍将继续下去。
朱炳昇,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 ◆ ◆
编辑邮箱:sciencepie@126.com